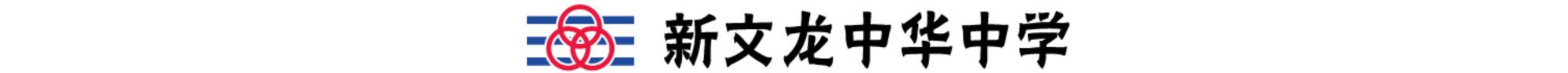《龙引十四年》
九、两渡重洋
小时候,我很羡慕大学生,尤其是文大学生;因为我们黄家那一族,只有三几个大学生;而外婆家的亲戚,多是武大学生,例如舅父、姨丈和姑外公都是陆军大学毕业的。我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进大学。我的双亲从来没有和我提过这些,当我高中毕业之後,我想进陆军机械化学校,妈妈也不曾反对;爸爸自己是军人,不想我走他的旧路;正像我不想我的女儿教书一样。
至於留学生,那更不必说了,我连做梦也不敢想像。战前要读四年大学,不卖掉十多石田是无法维持的。要到外国去留学,先要在国内大学毕业,出洋要一笔路费。这样一来,没有五千八千光洋,那是不可能的。
我的一位姨丈做过驻日大使馆武官,他是喝过海水的。另外一位族兄,是留法的勤工俭学生,不知他有没有进过法国的大学,至少喝过海水,算是留学生。在我的生活圈中,只有他们出过洋。如果再加两位:便是当时的教育厅长朱经农先生是美国留学生,姑外公的一位朋友徐庆誉博士也是美国留学生。在小学会考时,看见过一次朱厅长。在姑外公家见过两次徐博士;後来他在青年会公开讲演,我也跑去听了一次。想看一下留学生,似乎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多谢抗日期间的免费大学教育,我家没有卖掉一石田,我便大学毕业了。四年都是官费,妈只给我一笔赴重庆的路费而已。
在大学中,教授多是留学生。我没有想到要做教授,但是,我却想做一个留学生。在我大学毕业之後,当时有自费留学的考试制度,我不敢问津,官价外汇也买不起。我既是学外交的,将来到了外国,便可以找一间大学读书了。这种想法,相当幼稚。因为外放的人,在外国住了多年,很少有进大学读书的。
到马来亚後,看到受英文教育的多把伦敦当祖家,有钱的子弟都要去一趟;我反倒无此雅兴了。
在前面我曾提过:教育部曾召集一次华文中学正副校长的讲习会,当时的心理作战专家彼德逊讲演,大夸英国中学校教育为世界第一,有人提出: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英国去看看。他向提学司魏菲尔一指。那知魏菲尔竟大发脾气,弄得大家不欢而散•後来侯士先生为了打圆场;疏通英国文化协会出了一笔钱,约了一位华文中学校长去了一次伦敦。
墨甘霖问我为什么不去?我说:做梦也不敢想有机会用政府的钱去。我心中倒起了意念,我为甚么不到英国去留学?後来,美国新闻处的人来校参观,提到邀请我赴美。我也认为轮不到我,因为美国人处处从大地方着手,所以我一直在打算:迟早要去英国读书。
一九五三年,龙引开始办高师班,我做校长,却不是学教育的,很多东西都不明白,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对劲。五五年,教育局又要在龙引开办假期师训班,我必须做主任;我更感到我有赴英研究教育的必要。
我与振中先生商量,他非常赞成。那时的柔佛州华校总视学官耿威廉听说我有意赴英,便为我设法找奖学金。当时我还不是公民,又是做华校校长,我已不存奢望。想不到耿先生竞替我找到了中英奖学基金托管委员会的奖学金;由他们介绍,进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就读。我非常符合他们的条件:我是华人,已经大学毕业而且有学位,年龄也不大。唯一的条件是要我学成之後,回原留地服务若干年。对我来说,这不成为条件。於是,我在做留英梦了。
想不到耿先生介绍给我接头的驻星负责人回英渡假,我的姓名没有列入预算,要迟一年才能批准。这时大家知道我要赴英,我自己在心理上也有赴英的打算。突然不去,好像是一件丢脸的事;这一年也难熬。我忽然想到自己出钱去就不成问题了。耿先生劝我不必急,隔一年有奖学金不是更好。
我立刻与振中先生商量:我的薪津有八百元,四百多是小学新薪津制的校长职薪,让我领。教育局的薪津只够我在英的费用。我又和钱爱华兄商量,每月借我二百作家用。他一口答应,要我只管放心去,无论如何要请一个博士回来。後来我留英一年,考到一张教育文凭便回来了,他很失望。再隔一年,我将他借给我的钱,分两次还清,他也很不高兴。
董事长既然同意我去读书,我便将校务作一安排,准备就道。那知一切妥当之後,英国政府又不批准我入境,也没有说明甚么理由。後来找到墨甘霖替我担保,发了一个急电。那电稿的内容,他始终没有告诉我。
中英奖学基金托管委员会没有奖学金,连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学额也没有替我保留。我又赶去星洲。这时星洲代表由李绍茂先生代理,他替我写了一封信,;说明我自费赴英,替我找到了学位。
我向柔佛州当局申请有薪假期,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。某位朋友告诉我:振中先生和州秘书私交甚好,由他写信毫无问题。那知振中先生的信,由州秘书发下来,主管人员颇不开心,以为我们从上面压下来。我一时也按捺不下脾气,几乎吵起架来。结果又要我再写一封申请书,算是解决了。
新文龙三区董教分别设宴,热烈欢送。本校师生,更不在话下。峇株一些朋友,也不断邀约,饮宴无间。这一份盛情,我非常感激。十余年後的今日,我仍可回味。不过在当时,我倒是有些麻木。离情别绪,总是不能心安。第五个小孩即将出世,我要远离,使显敏多一重心理负担。我们已有四个女儿,虽然没有重男轻女的感觉,两个人的内心,自然都希望第五个是男孩,期待的焦灼,也使心绪沉重一些。
在另一方面,我也有前程似锦的感觉。我要去英国留学了,我也是留学生了。童年的幻梦,竟成了现实,我有喜乐,我有惊骇;我有满足之感:我也有不知所措之感!
振中先生同意我去,他没有问我要去多久。我先只作一年的打算,说不定三年五年。他没有问我学成是否仍回龙引继续服务,我也没有向他作出任何表示。在我们之间,似乎是心如灵犀一点通。用不着说得太明白。在我这方面来说,我对龙引学校没有任何义务,我只支政府的薪津,我没有拿董事会的薪水。
我离星赴英的那天,赴机场送行的至少有一百五十人,在星戚友已经是几十位,振中先生发动了董教学三方面,开了两辆校车去。我最怕惊动别人。在星戚友,我已是千辞万谢,请他们不要去送行。那知到了机场,黑压压的全是三区的人,我只有感动。因此也冲淡了离情别绪,仿佛是教师节的聚餐一般。
至今,我仍不明白振中先生为什么要热烈为我送行,因为他不是一个注重形式喜欢庸俗的客套的人。
在英国的那段期间,他还写过一两封信给我。有一次,我请他寄有关马来亚资料,他竟用航空邮寄了一大包。
我在英国时,茶叶吃完了,他也用航空寄了两斤给我。
这虽然都是小事,可是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想:也就是在这些地方,使人特别感念他。
他每日早起,一定要先喝一杯茶。他对於茶叶,相当讲究。我收到他寄来的茶叶那晚,我竟喝茶喝醉了!这也是奇闻。因为只有喝酒喝醉的。
晚上,我一面看书,一面烧水泡茶。茶叶是上等的,又是振中先生用航空寄来的,邮费都是卅余元。在心理方面,已有特别的满足。我那把茶壶是一位朋友送的廿五年以上的老壶,茶杯也是上品,其色如雪,其薄如纸。我又学会了一套功夫茶。一面泡,一面饮,一面看书。这才是真正的品茗,满怀欢喜,满口芬芳。喝了一壶,再泡第二壶,第三壶,第四壶………忽然我的头有点晕,我以为是看书太久。一看表,还不到十点,相当早。这时,好像要呕,又呕不出来。心中难受,好像生病—样。
我立刻躺在床上,可是又不能入睡,於是,我才意识到:我喝茶喝醉了。我立刻喝冷水,喝了几杯之後,才感到稍微舒适一点。很久以後,我才慢慢睡着了。
後来我和振中先生谈起这件事,他也觉得好笑。他每早喝的那一大杯浓茶,少也抵得两壶:我是够资格陪他喝的。如今,我仍用那把小茶壶在早晨泡茶喝。每次泡的时候,我就想到英国那次茶醉,因而联想到振中先生。
在英国那年的生活,可以说是多姿多釆的;我曾写了许多篇通讯,在南方晚报发表。後来印了一本英伦见闻。
伦敦大学的课业结束之後,我要显敏赴欧一游,把儿女都留在龙引。我俩从欧洲回来,我特别先写了了封信给振中先生,请他千万不要来接机,所以我不告诉他航机班次。其实我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,我的小孩们一定要接机,振中先生很容易知道我们抵达星洲的时刻。
我们走下飞机,已是黄昏时刻,因为防疫证书的事,我们留在检疫处很久。从玻璃窗中,只看到我的孩子们和几位亲戚。不,董事长也在向我摇手,还有一两位同事。半点钟之後,我们走到外面,哦,又和去的时候一样,黑压压的全是熟人:董事,教师和学生。
我说不出我是如何的感动!
我和教师及同学们打了一个招呼,他们又得赶快回龙引,因为那时还有戒严。董事长在上海饭店定了几桌酒席为我们夫妇接风;他们还得在星洲过一夜。振中先生很难得在外面过夜的。
从英国回来,教育局又要我们办假期师训班。我已有教育文凭,资格和经验都有了。不过,在龙引总是不方便。後来师训班设在新山,龙引去做讲师的,除了我之外,尚有陈植庭兄和王恢兄。我们三个人一直担任了好几届师训班的讲师。
龙引有一些人,认为我从英国留学回来,一定会另谋高就。事实上我也不是没有去处,但是我仍回原位。原因很简单:我和龙引学校已经有了感情,我和振中先生也有感情。
当我到伦敦不久,学校里转来一封美国新闻处的信,信上说如我有意赴美,可填表申请。我立即回了一个电报,说明我在教育学院读书,回马之後,再行联络,我回马的那年年底,学校里有五六位教师要离开,这是相当头痛的事。连钱爱华兄也要走;我与他竟是一别成了永诀。
振中先生似乎也遭遇到一些无谓的烦恼,我们仍是只谈如何处理学校内部的事,至於学校以外,他从不让我分忧;我也不曾多所过问。这也是他的伟大处:他分担我的烦恼,但他只让我分享他的快乐。
一九五七年学校开学以後,校务逐渐上了轨道。我们从香港请来了好几位老师,也加强了教师的阵容:尤其是文史方面,简直都是饱学之士,还有几位名书法家。於是,文风为之一振,学风为之一振。
大部份的老师都是住在校内,彼此往来密切。寄宿的男女学生相当多,师生朝夕相对处,潜移默化,移风易俗,感染较易。这样的环境,才是在真正的培育人才。
美国新闻处又来信问我有意赴美否?我和振中先生谈及,他认为机会难得,不可放弃。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廿几位在美国,我希望见他们,他们也希望见我。
奖学金是每天十元,一共半年。先到华盛顿作短期训练,以便对美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;然後分配到一间大学去研究三个月;接著安排一次长途旅行分派某一州去作教育参观;最後又回华盛顿作一次结业训练。
这种安排是很有吸引力的:可以进美国的大学读书,可以跑遍大半个美国,来往的飞机票都是头等的;在美国国内的旅行,在大学的书籍和学费,都由美国国务院负责。每天十元美金,只是食和住及零用,节省一点有得剩。
在我申请赴美时,也遭遇一点小麻烦,我没有办法参加甄别的面试,几乎不能入选。好在那位文化专员特别通融,由他打几个电话给那些甄拔委员,说明我的资历和学历,我既是伦敦大学的留学生,英文是没有问题的,不用面试就把名字补上了。
向教育局请假半年,很容易就批准了。这一次,振中先生和几位董事商量,我可以支全薪;因为校务由曾锦祥兄代理,我赴美,有奖学金;家用有校长的薪水。在经济方面,算是毫无问题。这时我深深感到董事长和诸位董事对我的厚爱,的确是难能可贵的,所以在欢送的宴会上,我用不纯正的闽南话说:我非常感激他们的爱护,我从美国回来,决意仍为学校服务,不会见异思迁的。
走的那天,不用说,又是盛大的欢送•董事长还在星洲机场餐厅招待所有来为我送行的人,连我的戚友在内。他的盛情,使我感激:他的慷慨,使人佩服。我的一位亲戚对我说:你们的董事长真大方,这一顿早点,少也得百多块!我听了是多么的舒服!我心中是多么的骄傲。
我真幸运,被分配到哈佛大学的教育研究院。我们的主要课程——教育行政是和那些读博士的一齐上课。
在中国,我读的是政治大学,以管理严格出名;在英国,我读伦敦大学,以能适应时代而出名;到美国,哈佛大学以古老而出名。三个国家,三个大学;三种文化,三种风格。
在美国半年,我写了许多篇游记,有的在蕉风发表,有的在学生周报发表。後来印了单行本,题曰美游杂记。
振中先生曾有两封长信给我,都是讨论学校的事。因为我四处奔跑,那两封信也没有留下来。更想不到他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,如今连他的遣墨都没有。後来清箱到箧,找出一个半个信封来,上面有他写的几个字,我已经把它当宝了。
三年之内,两渡重洋;环绕地球一周,只缺了大西洋。求深造,游世界:无後顾之忧,无经济之患;岂只是人生快事!简直是可遇难求了。公也好,私也好,都是得力於振中先生。古人云:人生得一知己,死亦无憾。我可以说是死亦无憾了。但是想不到振中先生先我而逝,使我终生抱憾。振中先生泉下有知,定能了解我的一片诚心!
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
振中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